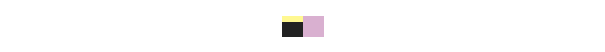只要还有人读书,张爱玲就永远不会消失|百年诞辰(上)
今天是作家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没有像许多人断言的那样被遗忘、被抛弃、被否定,反而愈加被重视、被欢迎、被肯定。在那个文学全然政治化的年代,张爱玲为中国文学保留下一颗珍稀的火种。
如本文作者文珍所言,只要现在、日后、更久远的未来还有人在读书,张爱玲就永远不会消失。
临水照花人的尤利西斯
谈张爱玲的后期写作
撰文:文珍
尤利西斯就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即便肉身无法回归,魂魄也要万里寻亲,寻最初的往生和来路。
1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台湾开始,她已如同任何一个被过度波普化的偶像一样,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恰当不恰当的地方:好比切.格瓦拉的红黑头像象征革命、自由与正义,也可能仅仅只是一张代表反叛姿态的旅行明信片或海报;毛泽东像章成为西方垮掉一代的个性图腾;梦露的白裙代表永恒的玫瑰与性感,时常也不无轻佻地暗示消费主义时代女性的日益被物化。
而她,则作为最后的海上传奇和最著名的民国女子,无数假她之名的金句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然而多半连腔调都没有学像。各大网站每逢她的忌诞生辰也多推出图文并茂的纪念专题,里面却往往错夹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她有关的轻性散文更是不胜枚举,却往往只翻来覆去纠缠于那场著名的情爱官司讨论男女攻防之道。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不认得她,却仍一直堂而皇之地消费她:只因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名人,任人涂抹的偶像,却鲜少有人肯把她还原成一个单纯的创作者。
起初我认识她,也只不过是低垂的单眼皮,睫毛阴影像蝶翼一样轻打在瘦削长圆的鹅蛋脸上。另一张常见的照片上,她双手插腰,冷眼斜睨世人,眼睛里并没有想要取悦谁的神气,但是写人人都爱看的小说。
有人说见她之后,才知道原来“艳也不是那艳法,惊也不是那惊法”。只好笼统说成是临水照花人。还是她提醒他可以用宋江赞九天玄女的话形容自己,“天然妙目,正大仙容”。仿佛自恋,但一看也知道是在有恃无恐的爱中——尽管情缘短暂,尽管彩云易散琉璃脆。
她早年的照片还有一张是童花头挤在两个女眷中间——一个是她妈妈,一个是她姑姑。齐刘海下的圆脸抿出乖巧的微笑,远看不出来后来的特立独行。并且胖,并且看上去对这个世界满意。
最后一张就是临去世前两月拿着金日成去世讣闻的照片了。眼睛里忍笑的光似乎还在。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比起她最鼎盛风光的时期,这照片也已经整整老了五十年。半世纪以来她行迹难觅,公开发表的近作亦寥寥。然而因为命运安排的种种离奇,这个被文学史错过几十年的名字,旧作佚作再度被人从故纸堆里逐一翻检出来,重新奉为圭臬。
她人还活着就早早封了神。
甚至去世二十年后,她的名字依是报纸副刊和新媒体的阅读量保证。海内外无数文学从业者自发替普通读者追踪她后半生的行踪,细数她赴美早期的出版挫折和职业打击,研究她与友人事无巨细的通信,又不厌其烦工笔描摹出一个心如古井孤寂度日的晚年形象。最疯狂的案例,则是一九八零年某记者搬到洛杉矶她的寓所隔壁,每天翻检她丢出的垃圾,完成一篇所谓侧写报道——然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小说,不是她的。
是的,说了这么多,我说的正是她:Eileen Chang。本名张瑛,后为张爱玲。
▲张爱玲(1920 年 9 月 30 日 — 1995 年 9 月 1 日左右),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
一个名字的诞生或许只是出于偶然。而一个名字的传世却多半是一个人曾奋力创造以抗虚无的明证。
2
这无疑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写的文章之一。比任何论文、小说、散文、诗歌都要更难,因为对象是她。
和所有人一样,我早看惯她的奇装异服,清楚记得她讥诮世人的笑,听说过她“身材怎会这样高”,知道她爱吃“司空”面包却不喜下厨,通感力好到可以闻见桃红色的香气,会弹钢琴也会画画,写过剧本并想过以此谋生。然而如此种种全是皮相,全不重要。正如她写给夏志清的信里说:你知道的,我得到的世间好意全来自文章。——原书不在手边,意思大抵如此。
非但得到他人好意来自文章,我想她一生中自己的大多数狂喜,也多半来自懂得她文章者的“连朝语不息”。第一个公开的张迷,就是她第一个爱人。她早年说但凡报上夸她,说得不对她亦高兴,文章会一一剪下留存。到晚年她却对追捧避之不及,想起当年的话也许要啼笑皆非——寂寞了这么些年,作家也许如藏在阿拉丁神灯里的巨人,有报复迟发现者的快意。
抛开作者心情不提,根据断点印象快速勾勒一个人物生平也是容易的:早年只觉“出名要趁早”。五十年代起意图以英文写作打开欧美市场终至幻灭,靠翻译、创作剧本只可糊口并不扬名,研究求职屡屡受挫,六十年代访问台湾时,寄希望能靠写张学良赵四故事转运也无果而终。晚年她彻底隐居,每日受困于“咬啮性的小烦恼”,而将那些改了又改总不肯示人的晚期作品压在箱籄,甘愿领受外界江郎才尽的猜测。——事实大抵如此。人证物证也一应俱全,然而非要我用自己的话把这些重说一遍又有何意义?
这十几年来写过关于她的文章,除了一篇《异乡记》的三四百字读书笔记,不过一篇比较《十八春》和《半生缘》版本的短文,也不到两千字。越喜欢的越不知从何谈起,就像最在意的人往往说不出口那个最要紧的字。这些年她的书有几本也一再重看,却也并不觉得一定要为之写些什么。真要动笔了,才知道自己原来离一个合格的“张迷”境界还远,世上早有无数比我更肯花功夫在她身上的人。书越看越多,最终只发现自己仍然无话。
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因桃花本是最明艳生动的花。而张爱玲难写,也是同样。所有的话似乎都已说尽。女性观,文学观,情爱观,佛洛依德心理,反抗父权意识,乃至于月亮太阳种种意象,都早有人大费周章做了论文,中间不乏真知灼见者,林林总总,完全不差我这一篇。然而吴琦是这样一个合格的主编和出色的催稿者,绝不肯让我反悔自己年初在“张爱玲之夜”后信口说的话,又提醒这一期《单读》的主题是“消失的作家”,她正好合适。
天涯海角,有个名字在牵我招我,一再唤我回去。
已经有这么多人找过她、写过她了。而她还必得要我再找一次。
找她就是找自己,也许。厘清一个志业写作者可能遭遇的一生:这诱惑之大我躲不过去。
3
张爱玲最先叩问海外市场的作品是《秧歌》和《赤地之恋》。前者的英文版 The Rice-Sprout Song 勉强算小获成功,后者完稿后却迟迟卖不出去,作者给出最窝囊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名字全是三个字,外国人分不清——却无视俄罗斯人名显然更冗长,并不影响他国阅读的事实。归根结底还是人离乡贱,欧美读者没耐心,不买账。
她以前从没这样费心取悦过读者。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饱读中西诗书,又有不世出之才,把亲戚间遗老遗少故事改头换面,便足以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文坛“最美的收获”。
胡兰成曾问过她有什么是写不了的,“答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
势必要遇挫之后才知此一时,彼一时。但在人矮檐下,却也不得不低头。
▲《张爱玲全集(赤地之恋)》
张爱玲 著
大连出版社 出版
1996
有人说张爱玲写作英文比中文耐心完整,的确如此。但《赤地之恋》艰难付梓之后几乎没有反响,偶有评论也很尖刻,说“里面的人物让人作呕”。作者的苦心孤诣完完全全明珠暗投,陌生读者对她曾经的盛名毫无认识,对小众题材繁复意象显而易见地缺乏兴致。他们要看的也许是明白晓畅又符合人性最大公约数的,“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使得人类的同情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的作品,比如凭《大地》摘获 1938 年诺奖的赛珍珠;抑或是战火纷飞中富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异国传奇,比如韩素音的《瑰宝》;再不济,因“赤祸千里”而饱受荼毒的中国社会速写也能满足部分对他国局势好奇其实却早有成见的读者。然而张爱玲所能提供的一切全不合式。饶是她已做出了对于时局批判的最大努力,也依旧要被美国杂志批评她“把旧社会写得这样坏,岂不是说共产党英明”?
张氏特有的华丽苍凉,软弱不彻底的主人公,愈往后愈“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情调纯然是中国古典式的,原本就不是放之世界而皆准的美学,离开本乡本土就要害水土不服:与其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妨从读者接受理论分析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
而她却没有想到从小向往的文明世界,读者的西式肠胃竟不能够消化她特供的中式珍馔。这打击之大非同小可,即便正处于创作盛年的作家,也同样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方能真正接受。
而对于当时各种运动甚嚣尘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国内,去国之举已相当于在建国后的文坛自动除名,这两本书更等同于给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投名状,中文版至今无法出版,张爱玲写时大概也从未想过要再回头。然而出师未捷,我们可以想象她彼时的进退维谷:就像古代书生穿越到现代,陡然发现自己的锦心绣口经世雄才再无用武之地。她从此不但在她所不擅长的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连在最引以为自傲的文字世界里,也随时可能沦为边缘弃卒,最可悲的异国过气作家。
现实的风刀霜剑之下,张爱玲不得已提笔继续重为中文读者写作。而这时的中文出版市场已急遽萎缩,她的创作只能暂时先供应相对有限的港台读者。《五四遗事》就在一九五七年发表在夏济安、宋淇等人编辑的《文学杂志》上,算是她在台湾刊登的第一篇小说。
去国方始怀乡。如果说她的中后期写作是一场艰难无比的奥德修斯重返自身之旅,也许正可以从这篇不算引人注目的《五四遗事》说起。
4
张爱玲当时或许已知胡兰成在台湾,却偏写了一个三美团圆的故事。“小团圆”的若干同主题变奏曲初现端倪。
这篇与华美的早年风格相比,文字已趋洗练,而情节则愈见婉曲。人物一开始的动心都是真的,罗和密斯范西湖同舟的脉脉含情仿佛也足够用个十年八年。在柏拉图式的恋爱维持了一段时间后,男女主人公双方都感到关系再进一步的需要。
当天她并没有吐口同意他离婚。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楼外楼吃饭,罗已经感到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之夕,同时觉得他已经献身于一种奋斗。
然而罗回去之后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
他向妻子开口提出离婚。她哭了一夜。那情形的不可忍受,简直仿佛是一个法官与他判处死刑的罪犯同睡在一张床上。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辩护,他知道他是判她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
这一段不禁让我想起哈金的《等待》出色的开头:“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而哈金毕竟比张爱玲幸运得多:他所处的时代,西方人已经有较多耐心和同理心对待中国婚恋现实的复杂与独特性了。
回到《五四遗事》。在漫长到无望的等待中,密斯范迫于家庭压力与当铺老板相亲。然而罗此时其实已离婚在即,甫一成功立刻借媒妁之言负气娶了别人,而密斯范婚事并不顺利。这时又有好事者安排范罗重逢。果然他们也就如电影小说常见桥段般迅速旧情复炽起来:“罗这次离婚又是长期奋斗”。此前多是限制视角的男主人公单方面描写,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密斯范的心理分析:
密斯范呢,也在奋斗。她斗争的对象是岁月的侵蚀,是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而且她是孤军奋斗……结果若是成功,也要使人浑然不觉,决不能露出努力的痕迹。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她改变,要她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然而男子的心理是矛盾的,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发觉她变老式,落伍,他也会感到惊异与悲哀。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
笔调颇为轻快,然而背后却有无尽哀矜——我们也许记得《小团圆》里,盛九莉最初对邵之雍也有强烈的崇拜——很难说此处并没有作者本人的心理投射。果然他们历经磨难结婚后,一切过往情愫都因为对现实的失望迅速败坏。罗失望于密斯范不再讲究妆容,而密斯范犹如绷紧太久的弹簧陡然松开,出恶声说罗不像男人。此处叙述转急而字字刻毒:罗重新想起前两个妻子的好处,听人劝说陆续都接回同住——即便“从前的男人没有负心的必要”,但这故事也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十几年后了!这正是这小说甚至胜过《金锁记》的平静恐怖之处:罗反抗若干年,最后对荒诞现实非但全盘接受,甚至比一般人更进一步;密斯范虽然哭闹着要自杀,到头来依旧设宴招待两位情敌的娘家——也许是自恃地位已足够安全了。
《五四遗事》的英文版名字比中文版名字更一目了然:
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当自由恋爱最初进入中国
这漫画式的速写短篇,一方面也许为讽刺过渡时期中国新旧思想混乱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可视作作者对自身情事的首次翻案,以及对同时代若干同性的怒其不争:比如周训德,抑或范秀美。换她自己,这情形自然是不能容许的:因为热情的丧亡,因为情感的背叛,因为局面本身的“嘈剁剁,一锅烩”。但事实上她自己也差一点就沦落到了这地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说,“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也不会吃醋。”又说张曾对他表白,“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也都可以。”这无可无不可的风流自赏对比后来《小团圆》里九莉的万念俱灰,尤显残忍可笑。
然而无人能够拔起头发来脱离自己的时代。邵之雍不能,盛九莉不能,张爱玲同样不能——作为创作者的唯一可安慰处,在于可以一遍遍通过文字检视内心与过去的距离,无数次变形重说,同时祛魅,消弭,解构,放下。

内容来自网友分享,若违规或者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所有跟帖: ( 主贴楼主有权删除不文明回复,拉黑不受欢迎的用户 )
进入内容页点击屏幕右上分享按钮
楼主前期社区热帖:
- 派我的马甲和你们PK一下 03/20/22
- 只要还有人读书,张爱玲就永远不会消失|百年诞辰(下) 09/29/20
- 史上最好的故事之一,只有六个单词 09/29/20
- 为什么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 09/19/20
- 如何写砸一篇小说? 09/19/20
- NBA最佳阵容出炉:勒布朗字母哥获全票 LBJ创纪录 09/16/20
- 苏州最“低调”园林,风光堪比拙政园,入选世界遗产却少有人知 09/14/20
- 实拍江浙沪最纯真的古镇之一 这里有诗与远方 09/12/20
- 决策分析:债务和赤字高企、竞对蠢蠢欲动 美元恐陷入困境之中、人民 07/05/20
- 高盛将挪威克朗视为把握美元疲软趋势的最佳选择 07/05/20
- Beyond:跨越代沟的经典,你和00后都还在听吗 07/05/20
- 力压《烂柯棋缘》,吊打《遮天》,这本小说登顶热销榜仙侠类榜首 07/05/20
- 豆瓣8.6,不停反转的真相,这本书写透人性的黑暗! 07/05/20
- 当年进不去电影殿堂的冯小刚,选择在旁边支一顶帐篷 07/05/20
- 谈谈网络小说 06/18/20
- 6位编剧转型小说创作,《血色浪漫》排名第一,情节最俘获人心 06/18/20
- NBA球员将佩戴智能戒指 可提前三天预测新冠症状 06/18/20
- 现役哪些球员退役会立雕像?库里诠释一人一城,詹皇或3队一起立 06/18/20
- 曼巴PK答案!湖人官方晒科比和艾弗森同框照片 06/18/20
>>>>查看更多楼主社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