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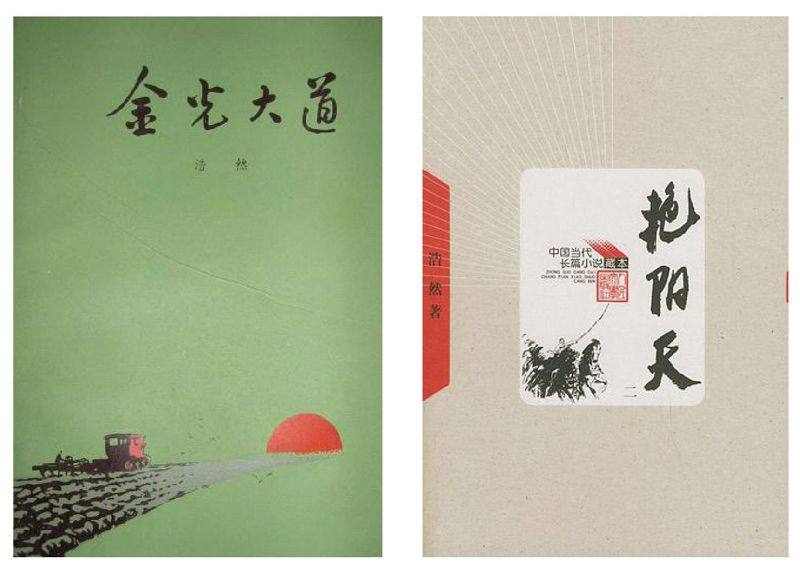  浩然(梁金广,1932~2008年)走了,像左倾年代众多名角一样,留下一长串说不清理还乱的是是非非,成为难解谜题的中国式“罗生门”——“浩然现象”。浩然走了,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车站。雷达先生说浩然“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其作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从而使小说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一定的艺术性与偏执的左倾视角构成“浩然现象”的两翼。原本就有点复杂的浩然,晚年又执拗坚持左偏观点,无论对其作品还是对已被历史否定的农村捆绑式合作化公社化,仍一往情深,挟“公社”以升天,抱“合作”而长终,更为“浩然现象”注入历史复杂性,具有相当的标本意义,值得后人弯腰一探。一、成名地基儿童团长出身的浩然正规学历仅小学三年半(三年小学,半年私塾),14岁就娶过一回媳妇。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浩然硬是成长起来,二十岁在蓟县基层工作时,顶着“作家精神病”的外号写稿投稿,最后成就一段二十年的大红大紫。直到他已成为专业作家,一直认为他不老老实实种地过日子的乡亲们,才终于承认他努力的价值。当然,浩然赶上了他的“好时候”——1950~1970年代的左倾大潮。“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耸然独立,群英低伏。沈从文、茅盾、丁玲、巴金、赵树理、曹禺……无数英雄竞折腰,唯浩然一峰挺立。浩然的阶级出身及农村题材恰吻“时代需要”,成就这位冀东蓟县弟子的人生辉煌。若无反“右”——“文革”这一历史大背景及阶级出身这一地基,浩然怕是无论如何站不上“一个作家”的绝巅,无论如何不能在众喉哀哑之时还能独家歌唱。浩然晚年说自己对革命的“信念,在一瞬间扎根”,十分直率地详述这份天然优越感:“以后我被时代的大潮卷进献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行列,再以后我倾心于文学创作,那种早就扎了根子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下意识地起着一定的作用。尽管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增长、经验增长,以及真正的革命性和唯物史观的确立,因而曾经努力地用最伟大最无私的观念管束和规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强制自己沿着最美好、最干净的轨道塑造自己的灵魂、移动人生脚步,然而那种优越感、满足感依旧顽固地、阴云不散地、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干扰着我,折磨着我;十有八九将要跟我同生共死,为此苦恼与怨恨也无济于事。”失去这份优越感与满足感,浩然能愿意么?心底会不起波澜么?能服气么?那可是真正的“失去天堂”呵!要浩然先生反思成名的历史衬垫与左倾地基,剖析极左思潮的反动性,需要较深的理论修养与较高的理性自觉,而这些是浩然所不具备或难以具备的。浩然成名的左倾地基成为制约他进行反思的强大“反作用力”,使他无法走出庐山之限。因此,晚年浩然多揣委屈而少忏悔,多惦着昔日辉煌而少真诚反省,凝塑为真正的“思想悲剧”。《浩然口述自传》采写者郑实说:浩然讲述奋斗成名经历时很有激情,说到“文革”就不那么顺畅,只强调“太复杂”,对世人最关心的这一段,讲得不多,也不够仔细。对“文革”讲的不多不细,或不愿讲,盖因觉得很难说,理不清。浩然晚年总是对来访青年说:“我的心很乱。”说明他无力对那一段历史与自己的一生进行宏观梳理,于是采取整体回避姿态。成长于左倾地基的浩然,当然只能是一根左扭之果。浩然先生偏偏不愿承认这一点,还执拗地以左为正,从而成为“浩然现象”的一大症结。二、幼稚思维与其他众多左派人物一样,他们的“复杂”源于他们的幼稚简单。他们将复杂万分的社会变革简单地视为“主义至上”与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坚定信仰与“内心爆发革命”,便一切OK。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造社会,其实就是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了,社会也就自然改造好了。“复杂的浩然”其实思想单纯,只是极左思潮的“简单信仰者”。据笔者近年对左倾人士的研究,如今仍持左偏观点者大多为八十左右的老人,信息渠道封闭,知识结构单一,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现实,既不认识资本主义也不知道社会主义,既不通晓国际共运也不熟悉现代思潮,既不理解社会变革只能是点滴增量的一个过程,也缺乏好心也会办坏事的历史警觉。他们成为赤左思潮退落后残剩的“社会意识”,不愿面对这场已然失败的运动,不承认他们的时代已是历史翻过去的一页。如托派老人郑超麟(1901~1998年),1990年还在盼望“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爆发”。2000年,浩然《口述自传》记述:1949年春在地委党校看了一部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整个党校沸腾了——第二天清晨……这个清晨特别晴朗,霞光特别鲜艳。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用吃过饭到上课前的那段空闲时间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全国农民都不破产,让他们的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诉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近古稀的今天,都在长,都在长;这期间,尽管有过动荡的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我还能够呼吸,那就绝对办不到。文革后,浩然不仅不认为自己弄错潮头,反而认为“躬逢盛时”: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特别是“合作化”,绝对属于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个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后人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绝非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浩然甚至坚持1956年“干预生活”确属逆流:“第二年春天,极容易走极端的中国文艺界气候骤变,一股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风耀武扬威地刮起。仿佛除了写这类题材和内容的作品之外,一律都不是文学。我的几篇自以为有所长进的新作,屡屡遭到报刊拒绝而不能发表。……由于我是在翻身农民和他们的先进分子基层干部中间成长起来的,加上年轻热情、积极向上,所以在生活中总爱看爱听光明的、鲜艳的东西,总爱想爱写美好、顺心的事物,新官僚主义者当然存在着,但数量少。”浩然一直如此看待1956年的“干预文学”,怪不得他终生难以走出深深左巷。浩然当年曾赶时髦写过一篇“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梯子》,幸而生活不足没成篇,“事过多年,每每由什么事情引起回忆,我还有一种心颤身抖般的后怕,当年我要是下苦功夫硬把《梯子》写出,写得顺手了再写几篇,我大有可能跟北京文学界的几位老兄老弟一样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喜鹊登枝》却成了我实现理想成名成家的‘梯子’。这一出本来应该以悲剧告终的戏,魔术似地变为喜剧结果,那么我主要应该感恩于何人,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可见,浩然确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格格不入,境界甚低——以个人一己私利划别是非。执守这样的逻辑起点与自恋情结,还能进行稍微深入一点的历史反省么?三、坚不认错1994年《金光大道》再版,上海青年评论家杨杨撰文《痴迷与失误》(载《文汇报·笔会》1994年11月13日),认为“作品本身从头至尾充斥的豪言壮语及陈旧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文革’特有的……《金光大道》与其说在表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农民的伟大、正确,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是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的佯装幸福感,那种空洞的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浩然好友刘绍棠也当面批评:“《艳阳天》好,把看家的本领全拿出来了,但《金光大道》没金光。”杨杨评语基本概括了当代读者对《金光大道》的感觉,尤其是经历反“右”——“文革”的中老年读者。但浩然对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1998年,浩然在《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作出回应: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予的机会……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代表人物。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这样,浩然就将自己参与“文革大合唱”所起到的历史反作用力说成正面作用力,不以为歪,反以为正,认定自己是“受伤的文艺战士”。如此这般,当然通不过当代评界的闸门,只能捧接“不中听”的评语。不过,浩然却从一位老外的奉承中得到安慰: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中国到处是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欣慰。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实在可悲!浩然的晚年判断力是真不行了。某些老外不知我国国情,用纯文艺眼光评论作品,而了解国情的“家里人”则不可能不从宏观看微观,一眼就能看出裹着的极左内脏。浩然也承认《艳阳天》、《金光大道》非常突出血统论。雷达先生近评《艳阳天》:“作家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主动脉,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不可能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不可能具备深沉的历史意识,只能把人物搁置在政治斗争的功利目的上,而这是浅层次的……政治需要压扁了艺术。”对浩然“文革”时期的作品(当然包括《金光大道》),评界批语则是“伪现实主义”、“伪浪漫主义”。浩然以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学“惟一”局内人自傲,但“惟一”就一定了不起么?一定具备必须膜拜的价值么?一段被否定的灾难历史能有多少正面分量?一场支付了4000万饿殍惨巨学费的公社化运动,你那个“局内人”还有什么骄傲资本?胸脯还挺得起来么?一段只能提供反面训鉴的“大时代”,你那鼓动歌颂的“文学事业”,还值得高举高悬么?别忘了,文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较之千万生命与社会大退步,浩然先生实在应该为自己的这份“惟一”感到惭愧,难以承受之轻呵!实在不该往外拎举吆喝。此外,据韦君宜“揭发”——“《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负责《金光大道》一书的编辑组长乃外单位红卫兵,新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看了稿子就说书中时间正值抗美援朝,怎么能不写上?“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编辑组长再次审稿时在四五页上每页添上抗美援朝,浩然向韦君宜抱怨:“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就这么一部创作时还需要为“保护艺术创作”而奋斗的编造型作品,不仅反映的合作化内容严重失实,严重违背生活真实,创作过程也毫无自由可言,怎么可能是一部了不得的“经典”呢?杨沫与浩然关系很近,杨沫之子老鬼评浩然:打倒“四人帮”后,他对自己与江青保持距离的那一面,强调过多,对自己作品中左的印痕那一面检查不够,对“文革”前农村受极左政策危害的那一方面,认识也不深,因而知识界的部分人对他的批评意见较多,其中有些人也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浩然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只好一头扎到农村,远离知识界,也远离文联的同行。……你的代表作美化了五十年代农村大搞集体化的那一段痛苦历程……以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自居,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有问题。四、左偏视角浩然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对“人民公社”的讴歌,虽然他经历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那场惨烈大饥饿。其时,他下放山东潍坊昌乐东村,每月定粮27斤(社员18斤),饿得一次上县城开会,连吃11个馒头,担心太撑才歇口。社员们却饿得吃树叶嚼青麦,《浩然口述自传》详细记载了那一时期的饥饿场景。众所周知,合作化公社化极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粮产量连年猛跌,乃是大饥饿的致因。薄一波提供的数据: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浩然仅因接触到几个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就对合作化留连忘返:“那个灾祸时期没在我的心灵里投下多么浓重的失望的阴影,更多的倒是希望的曙光。回到北京两年之后,动笔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浩然仍如此“正面”看待合作化公社化,仍视祸因为福因,这样的左偏视角,仍沉醉于对当年“新人新事”的浅俗欣赏,如何进行反思?怎么可能展开反思?浩然晚年还单极强调扶贫助弱,硬着脖子为合作化公社化立论:对于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于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这一两年里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对此,我不想辩驳。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今天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在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是真实的吗?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浩然晚年承认与当代社会有点格格难入,《口述自传》最后有一段:有些人好奇地问我,是否能理解当今的社会。问者大约觉得我和这个时代的距离太大了。我承认,是这么回事。我想自己只能尽力适应现在,努力溶合进这个时代吧。从上述引文中,可清晰看出浩然的价值持守——不可能也不愿意与自己的理想彻底告别。抽象地看,怀揣理想似无不妥,但问题是“理想”引发惨烈后果,拧歪了整个时代,也拧歪了自己。浩然身在歪处不知歪,扭着FeyRm33igAjm5NN7loTmtaQ7qfiym83JfwUrg85SZcE=脖子坚持谬误,这就不得不令后人起而指谬,一辨正误。不承认苦难,或在苦难面前转过身去,还有一点作家的良知否?判断现实应该是作家的一项基本能力,浩然在这方面如此低能,且以低为高,实在倒胃口。相比之下,赵树理1955年就开始质疑合作化。1956年8月23日,兼任县委书记的赵树理致信长治地委负责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相信我们县级干部都是勤奋勤勤恳恳做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好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受到好事之福,反而受到好事之累。赵树理50年前就看到浩然50年后还不愿看到的现实,甘愿背离“主流”,从“解放区文艺旗手”沦为“黑帮”并献祭生命。浩然则一直以“主流”自傲,称自己是吸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大的,1952年第一次读到时,“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它像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都融进我的心里。我的两眼亮了,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浩然在《口述自传》中毫不避讳“自觉自愿用文学为政治服务”,要为《金光大道》的“待遇”翻案,这种以耻为荣的态度,自必激起盈天沸反,毕竟时代不同了,欣赏左者浩然的人们大大减少。民间批评说“浩然就是五十年前的周正龙”。“浩然以农民作家自居,然而那些在1960年饿死的农民认可他吗?浩然笔下的农村现象,现实中真实存在吗?……浩然在当时的国人面前展示的农村画面,比‘周老虎’还假。……我认为,浩然就是五十年前的周正龙。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你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批的是浩然作品,戳的是极左思潮。相对其他“文革”人物的个人品德,浩然在这方面引议不多,争论主要集中于作品的价值。批评者集中于其作品的思想性,认为浩然作品展示的合作化公社化场景反历史反真实,从而反文学。五、“复杂”实质复杂的“浩然现象”,其实也只“复杂”在浩然的坚不认错,以歪为正。公社化、公有制的背后矗立着的价值支撑可是阶级斗争学说呵!晚年浩然仍持左倾文论,坚持写“主流”写“光明”,其历史观、认识论基本五十年一贯制,且以左倾观点为当然理据,没有一点进步呵!《浩然口述自传》既无忏悔亦无反思,倒有不少自炫自耀。且不说人生修养,即使从智慧角度,浩然的层次也甚低。评家唐达成说得很清楚:“赵树理在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再也无法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进行创作,他走不下去了,而浩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样才出现了《艳阳天》以及后来的《金光大道》。”但浩然却始终一力推重《金光大道》,再三宣称《金光大道》为其“代表作”,较的劲儿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化公社化,还是要“阶级斗争”,只是形格势禁不便直言,但又不甘默默退场,转着弯儿憋着气儿要“蒸”这屉包子。说白了,浩然打心底里不承认那场运动的失败,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的失败,还在执拗地为“公社”招魂,认定合作化运动将再度掀起,《金光大道》将再放“金光”。不认输不服气,不认为走错了路,不承认左倾偏斜方向,浩然嘴里说的是《金光大道》,心里揣着的则是“价值自信”。众所周知,真正传世的经典之作,必须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且达到一定高度。虽说浩然作品有一点艺术性民俗性,但如此先天不足严重跛脚,怕是很难再得后人垂顾。“进入经典”,只能是浩然的一厢之愿了。一言以蔽之,“复杂的浩然”其实只在于浩然的坚不认错,而其之所以坚不认错,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仍如此冥顽不化,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提供了使他能够“坚持”下去的东西。毋庸讳言,浩然的“坚持”说明左倾思潮未遭到犁庭扫穴的涤荡,左倾意识形态还有许多耸然挺立的堡垒,许多似是而非的左倾逻辑还在公然行走,这些才是成就“复杂浩然”的真正复杂之处。说到底,复杂的浩然,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判认能力的低下,真伪正谬评判标准相差太大,且无力进行辨析。浩然的“复杂”,深刻说明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对立,说明左倾意识形态还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说明对左倾思潮“清扫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雷达感慨:“他的一身奇特地交织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训和矛盾……‘浩然方式’既复杂又有代表性。通过‘最后一个’,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丰富的。”“复杂的浩然”,那段红色文艺的“最后一个”,典型性、时代性齐备,“不二”标本。随着岁月推移与认识深化,浩然的“迷左”还会被一再提起,相信惊讶与迷惑一色,叹息共嘲笑齐飞。历史总是一再超出人们的想象。(相关简介: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更正张曙光:由于本人的疏忽,《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一文,有一史实错误。具体如下:《领导者》总第48期第168页第3段最后一句,“何建章夺权当了经济所的所长,《经济研究》成为清查的重点,并撤销了唐宗昆《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职务”。其中,“撤销了唐宗昆《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职务”有误。应更正为:“1988年年末,经济所领导班子换届,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坚决不让唐宗昆继续担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唐宗昆本人也因刘国光的打压,再加上工作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在编完1988年最后一期杂志后,辞去常务副主编一职,退出编辑部的一切工作。常务副主编由副所长冒天启接任”。特此更正,由此而给当事人、广大读者和编辑工作带来的不便和损失,本人深表歉意。转自《领导者》2013年第1期 浩然(梁金广,1932~2008年)走了,像左倾年代众多名角一样,留下一长串说不清理还乱的是是非非,成为难解谜题的中国式“罗生门”——“浩然现象”。浩然走了,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车站。雷达先生说浩然“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其作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从而使小说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一定的艺术性与偏执的左倾视角构成“浩然现象”的两翼。原本就有点复杂的浩然,晚年又执拗坚持左偏观点,无论对其作品还是对已被历史否定的农村捆绑式合作化公社化,仍一往情深,挟“公社”以升天,抱“合作”而长终,更为“浩然现象”注入历史复杂性,具有相当的标本意义,值得后人弯腰一探。一、成名地基儿童团长出身的浩然正规学历仅小学三年半(三年小学,半年私塾),14岁就娶过一回媳妇。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浩然硬是成长起来,二十岁在蓟县基层工作时,顶着“作家精神病”的外号写稿投稿,最后成就一段二十年的大红大紫。直到他已成为专业作家,一直认为他不老老实实种地过日子的乡亲们,才终于承认他努力的价值。当然,浩然赶上了他的“好时候”——1950~1970年代的左倾大潮。“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耸然独立,群英低伏。沈从文、茅盾、丁玲、巴金、赵树理、曹禺……无数英雄竞折腰,唯浩然一峰挺立。浩然的阶级出身及农村题材恰吻“时代需要”,成就这位冀东蓟县弟子的人生辉煌。若无反“右”——“文革”这一历史大背景及阶级出身这一地基,浩然怕是无论如何站不上“一个作家”的绝巅,无论如何不能在众喉哀哑之时还能独家歌唱。浩然晚年说自己对革命的“信念,在一瞬间扎根”,十分直率地详述这份天然优越感:“以后我被时代的大潮卷进献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行列,再以后我倾心于文学创作,那种早就扎了根子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下意识地起着一定的作用。尽管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增长、经验增长,以及真正的革命性和唯物史观的确立,因而曾经努力地用最伟大最无私的观念管束和规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强制自己沿着最美好、最干净的轨道塑造自己的灵魂、移动人生脚步,然而那种优越感、满足感依旧顽固地、阴云不散地、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干扰着我,折磨着我;十有八九将要跟我同生共死,为此苦恼与怨恨也无济于事。”失去这份优越感与满足感,浩然能愿意么?心底会不起波澜么?能服气么?那可是真正的“失去天堂”呵!要浩然先生反思成名的历史衬垫与左倾地基,剖析极左思潮的反动性,需要较深的理论修养与较高的理性自觉,而这些是浩然所不具备或难以具备的。浩然成名的左倾地基成为制约他进行反思的强大“反作用力”,使他无法走出庐山之限。因此,晚年浩然多揣委屈而少忏悔,多惦着昔日辉煌而少真诚反省,凝塑为真正的“思想悲剧”。《浩然口述自传》采写者郑实说:浩然讲述奋斗成名经历时很有激情,说到“文革”就不那么顺畅,只强调“太复杂”,对世人最关心的这一段,讲得不多,也不够仔细。对“文革”讲的不多不细,或不愿讲,盖因觉得很难说,理不清。浩然晚年总是对来访青年说:“我的心很乱。”说明他无力对那一段历史与自己的一生进行宏观梳理,于是采取整体回避姿态。成长于左倾地基的浩然,当然只能是一根左扭之果。浩然先生偏偏不愿承认这一点,还执拗地以左为正,从而成为“浩然现象”的一大症结。二、幼稚思维与其他众多左派人物一样,他们的“复杂”源于他们的幼稚简单。他们将复杂万分的社会变革简单地视为“主义至上”与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坚定信仰与“内心爆发革命”,便一切OK。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造社会,其实就是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了,社会也就自然改造好了。“复杂的浩然”其实思想单纯,只是极左思潮的“简单信仰者”。据笔者近年对左倾人士的研究,如今仍持左偏观点者大多为八十左右的老人,信息渠道封闭,知识结构单一,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现实,既不认识资本主义也不知道社会主义,既不通晓国际共运也不熟悉现代思潮,既不理解社会变革只能是点滴增量的一个过程,也缺乏好心也会办坏事的历史警觉。他们成为赤左思潮退落后残剩的“社会意识”,不愿面对这场已然失败的运动,不承认他们的时代已是历史翻过去的一页。如托派老人郑超麟(1901~1998年),1990年还在盼望“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爆发”。2000年,浩然《口述自传》记述:1949年春在地委党校看了一部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整个党校沸腾了——第二天清晨……这个清晨特别晴朗,霞光特别鲜艳。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用吃过饭到上课前的那段空闲时间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全国农民都不破产,让他们的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诉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近古稀的今天,都在长,都在长;这期间,尽管有过动荡的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我还能够呼吸,那就绝对办不到。文革后,浩然不仅不认为自己弄错潮头,反而认为“躬逢盛时”: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特别是“合作化”,绝对属于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个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后人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绝非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浩然甚至坚持1956年“干预生活”确属逆流:“第二年春天,极容易走极端的中国文艺界气候骤变,一股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风耀武扬威地刮起。仿佛除了写这类题材和内容的作品之外,一律都不是文学。我的几篇自以为有所长进的新作,屡屡遭到报刊拒绝而不能发表。……由于我是在翻身农民和他们的先进分子基层干部中间成长起来的,加上年轻热情、积极向上,所以在生活中总爱看爱听光明的、鲜艳的东西,总爱想爱写美好、顺心的事物,新官僚主义者当然存在着,但数量少。”浩然一直如此看待1956年的“干预文学”,怪不得他终生难以走出深深左巷。浩然当年曾赶时髦写过一篇“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梯子》,幸而生活不足没成篇,“事过多年,每每由什么事情引起回忆,我还有一种心颤身抖般的后怕,当年我要是下苦功夫硬把《梯子》写出,写得顺手了再写几篇,我大有可能跟北京文学界的几位老兄老弟一样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喜鹊登枝》却成了我实现理想成名成家的‘梯子’。这一出本来应该以悲剧告终的戏,魔术似地变为喜剧结果,那么我主要应该感恩于何人,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可见,浩然确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格格不入,境界甚低——以个人一己私利划别是非。执守这样的逻辑起点与自恋情结,还能进行稍微深入一点的历史反省么?三、坚不认错1994年《金光大道》再版,上海青年评论家杨杨撰文《痴迷与失误》(载《文汇报·笔会》1994年11月13日),认为“作品本身从头至尾充斥的豪言壮语及陈旧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文革’特有的……《金光大道》与其说在表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农民的伟大、正确,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是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的佯装幸福感,那种空洞的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浩然好友刘绍棠也当面批评:“《艳阳天》好,把看家的本领全拿出来了,但《金光大道》没金光。”杨杨评语基本概括了当代读者对《金光大道》的感觉,尤其是经历反“右”——“文革”的中老年读者。但浩然对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1998年,浩然在《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作出回应: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予的机会……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代表人物。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这样,浩然就将自己参与“文革大合唱”所起到的历史反作用力说成正面作用力,不以为歪,反以为正,认定自己是“受伤的文艺战士”。如此这般,当然通不过当代评界的闸门,只能捧接“不中听”的评语。不过,浩然却从一位老外的奉承中得到安慰: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中国到处是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欣慰。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实在可悲!浩然的晚年判断力是真不行了。某些老外不知我国国情,用纯文艺眼光评论作品,而了解国情的“家里人”则不可能不从宏观看微观,一眼就能看出裹着的极左内脏。浩然也承认《艳阳天》、《金光大道》非常突出血统论。雷达先生近评《艳阳天》:“作家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主动脉,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不可能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不可能具备深沉的历史意识,只能把人物搁置在政治斗争的功利目的上,而这是浅层次的……政治需要压扁了艺术。”对浩然“文革”时期的作品(当然包括《金光大道》),评界批语则是“伪现实主义”、“伪浪漫主义”。浩然以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学“惟一”局内人自傲,但“惟一”就一定了不起么?一定具备必须膜拜的价值么?一段被否定的灾难历史能有多少正面分量?一场支付了4000万饿殍惨巨学费的公社化运动,你那个“局内人”还有什么骄傲资本?胸脯还挺得起来么?一段只能提供反面训鉴的“大时代”,你那鼓动歌颂的“文学事业”,还值得高举高悬么?别忘了,文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较之千万生命与社会大退步,浩然先生实在应该为自己的这份“惟一”感到惭愧,难以承受之轻呵!实在不该往外拎举吆喝。此外,据韦君宜“揭发”——“《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负责《金光大道》一书的编辑组长乃外单位红卫兵,新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看了稿子就说书中时间正值抗美援朝,怎么能不写上?“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编辑组长再次审稿时在四五页上每页添上抗美援朝,浩然向韦君宜抱怨:“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就这么一部创作时还需要为“保护艺术创作”而奋斗的编造型作品,不仅反映的合作化内容严重失实,严重违背生活真实,创作过程也毫无自由可言,怎么可能是一部了不得的“经典”呢?杨沫与浩然关系很近,杨沫之子老鬼评浩然:打倒“四人帮”后,他对自己与江青保持距离的那一面,强调过多,对自己作品中左的印痕那一面检查不够,对“文革”前农村受极左政策危害的那一方面,认识也不深,因而知识界的部分人对他的批评意见较多,其中有些人也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浩然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只好一头扎到农村,远离知识界,也远离文联的同行。……你的代表作美化了五十年代农村大搞集体化的那一段痛苦历程……以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自居,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有问题。四、左偏视角浩然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对“人民公社”的讴歌,虽然他经历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那场惨烈大饥饿。其时,他下放山东潍坊昌乐东村,每月定粮27斤(社员18斤),饿得一次上县城开会,连吃11个馒头,担心太撑才歇口。社员们却饿得吃树叶嚼青麦,《浩然口述自传》详细记载了那一时期的饥饿场景。众所周知,合作化公社化极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粮产量连年猛跌,乃是大饥饿的致因。薄一波提供的数据: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浩然仅因接触到几个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就对合作化留连忘返:“那个灾祸时期没在我的心灵里投下多么浓重的失望的阴影,更多的倒是希望的曙光。回到北京两年之后,动笔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浩然仍如此“正面”看待合作化公社化,仍视祸因为福因,这样的左偏视角,仍沉醉于对当年“新人新事”的浅俗欣赏,如何进行反思?怎么可能展开反思?浩然晚年还单极强调扶贫助弱,硬着脖子为合作化公社化立论:对于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于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这一两年里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对此,我不想辩驳。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今天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在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是真实的吗?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浩然晚年承认与当代社会有点格格难入,《口述自传》最后有一段:有些人好奇地问我,是否能理解当今的社会。问者大约觉得我和这个时代的距离太大了。我承认,是这么回事。我想自己只能尽力适应现在,努力溶合进这个时代吧。从上述引文中,可清晰看出浩然的价值持守——不可能也不愿意与自己的理想彻底告别。抽象地看,怀揣理想似无不妥,但问题是“理想”引发惨烈后果,拧歪了整个时代,也拧歪了自己。浩然身在歪处不知歪,扭着FeyRm33igAjm5NN7loTmtaQ7qfiym83JfwUrg85SZcE=脖子坚持谬误,这就不得不令后人起而指谬,一辨正误。不承认苦难,或在苦难面前转过身去,还有一点作家的良知否?判断现实应该是作家的一项基本能力,浩然在这方面如此低能,且以低为高,实在倒胃口。相比之下,赵树理1955年就开始质疑合作化。1956年8月23日,兼任县委书记的赵树理致信长治地委负责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相信我们县级干部都是勤奋勤勤恳恳做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好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受到好事之福,反而受到好事之累。赵树理50年前就看到浩然50年后还不愿看到的现实,甘愿背离“主流”,从“解放区文艺旗手”沦为“黑帮”并献祭生命。浩然则一直以“主流”自傲,称自己是吸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大的,1952年第一次读到时,“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它像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都融进我的心里。我的两眼亮了,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浩然在《口述自传》中毫不避讳“自觉自愿用文学为政治服务”,要为《金光大道》的“待遇”翻案,这种以耻为荣的态度,自必激起盈天沸反,毕竟时代不同了,欣赏左者浩然的人们大大减少。民间批评说“浩然就是五十年前的周正龙”。“浩然以农民作家自居,然而那些在1960年饿死的农民认可他吗?浩然笔下的农村现象,现实中真实存在吗?……浩然在当时的国人面前展示的农村画面,比‘周老虎’还假。……我认为,浩然就是五十年前的周正龙。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你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批的是浩然作品,戳的是极左思潮。相对其他“文革”人物的个人品德,浩然在这方面引议不多,争论主要集中于作品的价值。批评者集中于其作品的思想性,认为浩然作品展示的合作化公社化场景反历史反真实,从而反文学。五、“复杂”实质复杂的“浩然现象”,其实也只“复杂”在浩然的坚不认错,以歪为正。公社化、公有制的背后矗立着的价值支撑可是阶级斗争学说呵!晚年浩然仍持左倾文论,坚持写“主流”写“光明”,其历史观、认识论基本五十年一贯制,且以左倾观点为当然理据,没有一点进步呵!《浩然口述自传》既无忏悔亦无反思,倒有不少自炫自耀。且不说人生修养,即使从智慧角度,浩然的层次也甚低。评家唐达成说得很清楚:“赵树理在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再也无法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进行创作,他走不下去了,而浩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样才出现了《艳阳天》以及后来的《金光大道》。”但浩然却始终一力推重《金光大道》,再三宣称《金光大道》为其“代表作”,较的劲儿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化公社化,还是要“阶级斗争”,只是形格势禁不便直言,但又不甘默默退场,转着弯儿憋着气儿要“蒸”这屉包子。说白了,浩然打心底里不承认那场运动的失败,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的失败,还在执拗地为“公社”招魂,认定合作化运动将再度掀起,《金光大道》将再放“金光”。不认输不服气,不认为走错了路,不承认左倾偏斜方向,浩然嘴里说的是《金光大道》,心里揣着的则是“价值自信”。众所周知,真正传世的经典之作,必须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且达到一定高度。虽说浩然作品有一点艺术性民俗性,但如此先天不足严重跛脚,怕是很难再得后人垂顾。“进入经典”,只能是浩然的一厢之愿了。一言以蔽之,“复杂的浩然”其实只在于浩然的坚不认错,而其之所以坚不认错,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仍如此冥顽不化,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提供了使他能够“坚持”下去的东西。毋庸讳言,浩然的“坚持”说明左倾思潮未遭到犁庭扫穴的涤荡,左倾意识形态还有许多耸然挺立的堡垒,许多似是而非的左倾逻辑还在公然行走,这些才是成就“复杂浩然”的真正复杂之处。说到底,复杂的浩然,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判认能力的低下,真伪正谬评判标准相差太大,且无力进行辨析。浩然的“复杂”,深刻说明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对立,说明左倾意识形态还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说明对左倾思潮“清扫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雷达感慨:“他的一身奇特地交织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训和矛盾……‘浩然方式’既复杂又有代表性。通过‘最后一个’,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丰富的。”“复杂的浩然”,那段红色文艺的“最后一个”,典型性、时代性齐备,“不二”标本。随着岁月推移与认识深化,浩然的“迷左”还会被一再提起,相信惊讶与迷惑一色,叹息共嘲笑齐飞。历史总是一再超出人们的想象。(相关简介: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更正张曙光:由于本人的疏忽,《反精神污染中经济理论界的两大事件》一文,有一史实错误。具体如下:《领导者》总第48期第168页第3段最后一句,“何建章夺权当了经济所的所长,《经济研究》成为清查的重点,并撤销了唐宗昆《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职务”。其中,“撤销了唐宗昆《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职务”有误。应更正为:“1988年年末,经济所领导班子换届,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坚决不让唐宗昆继续担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唐宗昆本人也因刘国光的打压,再加上工作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在编完1988年最后一期杂志后,辞去常务副主编一职,退出编辑部的一切工作。常务副主编由副所长冒天启接任”。特此更正,由此而给当事人、广大读者和编辑工作带来的不便和损失,本人深表歉意。转自《领导者》2013年第1期 |
内容来自网友分享,若违规或者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所有跟帖: ( 主贴楼主有权删除不文明回复,拉黑不受欢迎的用户 )
打开微信,扫一扫[Scan QR Code]
进入内容页点击屏幕右上分享按钮
楼主前期社区热帖:
>>>>查看更多楼主社区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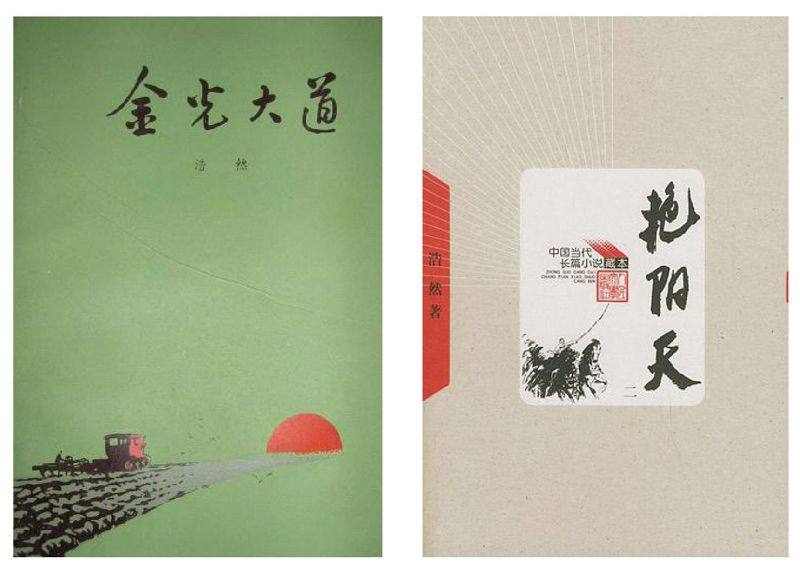

 请点这里投票,“赞”助支持!
请点这里投票,“赞”助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