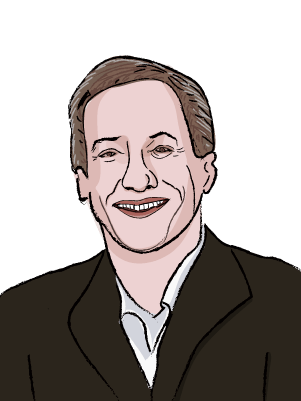一个幕僚眼中的拜登
https://www.sohu.com/a/447551356_354194
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乔·拜登当选为美国第46届总统。这位78岁的老人从政逾五十年,两度竞选美国总统,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履历丰富。新近出版的《下沉年代》一书中,作者乔治·帕克通过一位拜登重要幕僚的视角,回溯了他1988年和2008年的两次总统选举,及其政治生涯的许多大事。这位幕僚名字叫杰夫·康诺顿(Jeff Connaughton),在2008年美国大选为拜登贡献最多的人员名单中,康诺顿名列第三。
在大学时期,康诺顿第一次看到才36岁的拜登后,就疯狂迷恋上了拜登,发誓终生跟随他的脚步。此后的三十年,康诺顿时而成为说客,时而成为公职人员,穿梭于华尔街、竞选办公室和白宫之间。他以罕有的内部视角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拜登。
乔治·帕克是美国作家、记者,在他眼中,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就陷入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上的漫长解体,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就此不断下沉,《下沉年代》书写的正是这近三十余年的解体过程,以及其中一个个鲜活的人。
对于拜登,我们尚不得知他是否能修补这个撕裂的悲剧,但作为时间长河中的标志人物,却让我们得以窥见美国政治是如何剧变的。下文节选自《下沉年代》。
··············· ❶
1979年 “当总统的料”
1979年,杰夫·康诺顿第一次见到乔·拜登。拜登那年三十六岁,是美国参议院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参议员。康诺顿十九岁,是亚拉巴马大学的一名商科学生。
拜登身穿定制西装、打着红色领带出现在校园里,他风度翩翩,微笑时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白牙;在Phi Mu姐妹会(康诺顿的女朋友也是其中一员)的晚宴上,他迷倒了满屋子可爱的女学生。那天晚上,康诺顿作为拜登的助手坐在他身旁,此刻的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两百名学生来听拜登的演讲,学生中心被挤得满满当当。康诺顿介绍了拜登,然后在前排坐下。拜登走上讲台。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听说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拜登说,“没错,我是广为人知的所谓‘当总统的料’。”人群紧张地笑起来,为他的幽默感倾倒。现在,拜登吸引住了听众,他转向自己的话题,花了九十分钟清楚地解释削减美国和苏联核武器的重要性,反驳参议院中对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反对声音,全程没看一眼笔记。前一天,由于在古巴发现了苏联部队,谈判遭受了打击。“大伙儿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拜登轻声说道。他拿着麦克风走向观众,用手势示意他们身体前倾听他讲话。“那些部队一直都在古巴!”他大声说道,“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演讲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康诺顿站起身来,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谢,却无意间引发了全场观众跟着起立喝彩。
一个校园保安开车送拜登回伯明翰机场,康诺顿一同随行。因为演讲,拜登看起来很疲倦,但他深思熟虑地回答了保安的每一个入门级问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区别是什么?”),仿佛是大卫·布林克利在向他发问。当康诺顿问拜登为什么他每天都要搭火车从威尔明顿去华盛顿,参议员冷静地讲述了1972年12月那场几乎害死他全家人的车祸。事故发生在他当选参议员之后一个月。“我的妻子和小女儿死了,”拜登说,“儿子们受了重伤。于是我留在医院陪伴他们。我当时完全不想做参议员了。但最后,我在儿子的病床边宣誓就职。我是一名参议员,但我每天都会回家陪伴儿子们。这么多年来,特拉华州已经习惯了我每天都会回家。所以我真的没法搬去华盛顿。”
就在那一刻,康诺顿迷上了乔·拜登。他身上有悲剧,有能量,有雄辩口才——如同肯尼迪家族一样。拜登会对遇到的每一个人施展魅力,直到建立起某种联系,才会继续前行——姐妹会的女生,演讲的听众(许多学生参加演讲是为了拿学分),校园保安,以及那个邀请他来塔斯卡卢萨的大三商科学生。
从亚拉巴马毕业之前,康诺顿又两次邀请拜登(与数十名其他民选代表一起)前来进行有偿演讲,拜登每一次演讲前都会说同样的笑话,到第三次时,他的演讲已经价值一千美元。康诺顿最后一次送拜登到伯明翰机场时,他告诉参议员:“如果有朝一日您竞选总统,我会在您身边。”
图片来源 Gage Skidmore/Flickr
❷
1987年 “白痴”
1987年,本该把华尔街银行家送往财政部高层职位的旋转门,只让康诺顿在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中获得一个初级职位,年薪两万四千美元。他把全新的标致换成父母那辆1976年的雪佛兰迈锐宝,因为他还不起车贷了。对他来说,这些都无所谓。
他还没离开亚特兰大就接到第一项任务:在佐治亚州找到二十个人,让每人为竞选活动写一张两百五十美元的支票。如果在二十个州里做到这些,候选人筹得的款项就达到能够获得联邦配套资金的标准。这是康诺顿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但对失败的恐惧激励了他,让他去请求自己在佐治亚认识的每一个人写支票。他成功了,在这一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筹款:不必说服所有人相信拜登能赢,甚至不必说服他们相信拜登在议题上是正确的——只需要说明你需要他们帮个忙。“为我这么做。”关键在于是谁在打这个电话。不过,当他询问曾经是Phi Mu成员、现在住在佐治亚的前女友时,她拒绝了:她辗转听说拜登“为了当总统宁愿出卖自己的祖母”。
康诺顿在特德·考夫曼手下工作。考夫曼是拜登身经百战的幕僚长,身材瘦高,下巴尖细,头发蓬松浓密,如同埃尔·格列柯笔下的人物。
考夫曼和康诺顿一拍即合。两人都是MBA,他们决定要像运营公司一样运营筹款活动。康诺顿帮忙起草战略方案,设计了一套由组长和副组长组成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副组长筹集的资金越多,组长就能有越多机会接触到拜登。康诺顿记录着这场竞赛的进程,决定着谁能获得一枚胸针,谁又能与候选人共进晚宴。他还为捐款人也设立了一个系统。如果其中有人想见拜登,就得至少捐赠一千美元。康诺顿会告诉出手最大方的捐款人:“花上五万美元,你就能跟参议员在他家里共进晚宴。两万五千美元,你能跟参议员共进晚宴,但不是在他家里。”有些捐款人就会拼命多凑出两万五千万美元来,只为了能告诉朋友们:“我跟乔在他威尔明顿的家里共进晚宴了。”
康诺顿手绘像
康诺顿步步攀升,他在南方城市的出庭律师与犹太人社区中策划了多场五万美元级别的筹款活动。他开始与拜登一同旅行,每当飞机延误,或是拜登抵达后的讲话太长或太短时,康诺顿就会替他挡住捐款人的不满。他和拜登从未交谈。
有一天,在去往休斯敦一场筹款活动的航班上,康诺顿被安排向拜登简单介绍活动内容。他拿着活动手册,穿过飞机过道,来到拜登和他妻子吉尔所在的头等舱。
“参议员,我能跟您谈一会儿吗?”康诺顿问。
“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就行了。”拜登说,他几乎头也没抬。
拜登显然不记得亚拉巴马了。康诺顿为他工作很久之后,这位老板会搞错他们最初的联系,说:“我很高兴多年以前你还在法学院时就能认识你。”拜登总会花时间跟陌生人相处,特别是当他们跟特拉华州有关时更是如此。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或者是像考夫曼一样长时间为他工作的心腹,如果你像参议员爱说的那样“流着蓝色的拜登之血”,那么他也会对你表现出强烈的忠诚。然而,如果你只是为他鞍前马后忙上几年,他会无视你、恐吓你,有时会羞辱你,对你的进步毫无兴趣,也永远不会记得你的名字。他会冲你叫“嘿,长官”或者“怎么样,队长”,除非他对你动了气,那时他就会使用他最喜欢的男性下属称呼:“操他妈的白痴”。“操他妈的白痴还没把我要的简介材料拿过来。”这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这个活动领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说你们太白痴了连这也不知道?”
《下沉年代》书目
康诺顿所做的是艰难且必不可少的筹款工作,同时也得不到回报。为了这份工作,他遭受了永远的创伤,因为拜登痛恨筹款,痛恨它所带来的麻烦和妥协。拜登的同僚中,有些人似乎大半辈子都在打电话筹款——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哪怕在健身房里骑室内脚踏车时也在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就为了筹得五百美元——但拜登几乎从来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作为特拉华州参议员,他的整个州其实只有别的州一些县那么大,从来不需要筹集多少钱;他一直没能适应总统竞选中的财务压力。他痛恨那些帮他筹款和为他写下支票的人对他提出要求,仿佛他无法忍受自己欠他们什么。在华盛顿,他从不跟固化的上层阶级打交道,而是每天晚上都会离开国会山的办公室,穿过马萨诸塞大道走向联合车站,然后搭火车回到威尔明顿的家人身旁。他一直是“普通人乔”,这成了一种挑衅般的骄傲。他无法被收买,因为他不知感恩。
9月初,康诺顿从竞选活动中短暂抽离。他正开车穿过宾州乡村,收音机里传来了一则新消息:拜登在艾奥瓦州的一次辩论中抄袭了英国工党政治家尼尔·基诺克的演讲,甚至还照抄了基诺克作为煤矿工人后代的身份。
康诺顿并没有听过基诺克的演讲,也不知道拜登是如何运用的。说实话,他并不关心拜登的巡回演讲;他总能用一句话引发满堂喝彩:“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政治英雄被谋杀了,就说我们的梦想已经破灭,它深深埋在我们破碎的心底。”康诺顿比任何人都更敬重肯尼迪,但这句台词让他显得平平无奇——它太文绉绉了,更适合十年前或更久之前的美国人。为什么拜登不能让演讲更务实,谈谈议题、事实和解决方案,就像在塔斯卡卢萨谈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那样呢?
在竞选团队内部,基诺克的故事爆出之后的两周如同一场失控的噩梦,每一天都有新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但回想起来,结局的到来仿佛早已注定、无可避免,如同古代部落文化中核心的一场献祭仪式。候选人发誓要坚持,试图无视狂吠的猎犬。媒体则不停地抽血。候选人的同僚表示支持他。但这些故事已经树立起难以挽回的糟糕形象,可能再也无法抹除。候选人把家人和心腹聚集在身旁,一个接一个地询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希望他能继续参选,好保卫自己的名誉;他们希望他能退选,好保卫自己的名誉。带着泪水,他选择放弃。他压抑着怒火,扬起下巴,面对摄像机。
❸
2007年 “你每四年
只关心我们一次。”
十五年来,康诺顿为拜登筹集的资金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多。他加入拜登的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担任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团结我们的国家”的财务委员。这项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拜登轻率地对待他的政治演讲,那基本上是重复他的简历——每一站都很出色,却与下一站没有关联。他仍然讨厌金钱游戏。有一天,一名年轻的幕僚上车时拿着一份名单,告诉他:“参议员,该打几个筹款电话了。”拜登说:“你他妈给我滚下车去。”他认为,强有力的辩论表现能比私人电话给他带来更多的钱。三十年前在塔斯卡卢萨发表演讲后将康诺顿纳入麾下的政治家,在与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约翰·爱德华兹和巴拉克·奥巴马同台竞争时始终是强有力的存在。但他在民意调查中毫无存在感。
康诺顿在艾奥瓦州度过了12月。每隔两年,华盛顿永居阶级的成员都会来到“真正的美国”各地,为他们的团队竞选;“真正的人民”生活在那里。他们用这种方式建立备忘录,重新找回身为政党成员的意义。2000年的一天,早上6点,康诺顿在威斯康星州瓦萨奥的一个路口举起了戈尔的竞选标志,所有黑人司机和一半女性都竖起大拇指,白人男性则向他投来憎恶的目光,还有一辆满载儿童的校车司机差点把他撞翻。2004年,他花了三周在南达科他州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上门助选——每天工作十小时,令人厌倦到骨子里。贫困让他震惊:拉皮德城的许多拖车的地板都腐烂了,露出下面的泥土。
图片来源 Gage Skidmore/Flickr
在青松岭保护区附近,一位印第安女性告诉康诺顿:“你每四年只关心我们一次。”这句话灼穿了他,因为他知道这无比真切——每一个总统竞选周期中,他都会被像她这样的人的困境所打动,然后就把她们忘得一干二净。他试图向贫困地区的社区中心捐赠电脑,但达施勒的团队中没有人跟进。在这个国家的中部,他感觉不到能量,这里没有海岸和大城市的创业精神,仿佛所有的分子都在休息。晚上,他会在酒店里瘫倒,那里的酒吧挤满了华盛顿的说客,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暂居南达科他州。那年11月,达施勒输了。
在2007年的竞选活动中,康诺顿开始偶尔与拜登会面。有一次,在筹款活动之前,他们单独相处——康诺顿露出平日的微笑,说能见到参议员真好,并清楚地告诉参议员,他即将面对哪个团体。拜登突然盯着康诺顿,目光中带着疑惑,仿佛在问:“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们不是朋友吗?”
拜登这样的竞选是一种集体自我妄想。拜登的资深顾问特德·考夫曼告诉康诺顿:“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你要么就得假装,要么就死定了。”2008年1月3日,康诺顿在滑铁卢附近的一所高中监督艾奥瓦州的党团投票。大约有八十人站在巴拉克·奥巴马投票处的角落,六十人站在希拉里·克林顿那里,六个人站在乔·拜登那里。拜登在艾奥瓦州以百分之零点九的得票率获得第五位,当晚就退出了竞选。他向幕僚索要了对他的竞选活动帮助最大的人员名单。康诺顿名列第三。
康诺顿已经假装很久,此时他感到彻头彻尾的解脱。他合上了萦绕自己生命三十年的假想账本。他与拜登到此为止。
❹
2008年 “咱们做到了,伙计。”
当拜登在2008年夏天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康诺顿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美国最大规模游戏内圈的外围。这场游戏如此盛大,他毫不犹豫地重新打开拜登这册账本。赛马再度举行,仍旧是那令人眩晕的上下起伏,但这次速度更快,更令人目不暇接。在丹佛举办的党内大会上,他原本待在城外十五英里的宾馆,是个毫无作用的流放者,如今却摇身一变,开始审查拜登酒店套房周四晚上贵宾派对的客人名单——他让其他前工作人员知道,他既能放他们进去,也能将假装忠于拜登的人拒之门外。在派对上,他等着轮到自己,最终等到一只胳膊钩上他的肩膀。“咱们做到了,伙计。”拜登说。
每当康诺顿开始滑向外界的黑暗,他的手机总会响起,将他拖回来;那个电话总是来自特德·考夫曼,他在华盛顿不可放弃的盟友。考夫曼接续拜登的下一届参议院任期的前两年,他邀请康诺顿担任自己的幕僚长。年届五十的康诺顿接受了工资的大幅削减,回到参议院。
考夫曼只会做两年参议员。没有选举像铡刀一样悬在头上,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必把一半的晨间时光花费在K街的筹款早餐会上。康诺顿也感到自由:他已经兑现了一次支票,如今已不必一边接听说客的电话,一边盘算自己的未来职业前景。他们都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查华尔街,而不必担忧后果。“就算我需要竞选连任,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告诉记者。可是康诺顿在华盛顿待了太久,已经不相信这种言论。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也正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经济衰退中,数十万个工作岗位正在蒸发。
康诺顿不安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旋转门和互利互惠如何运作,也知道当权者潜意识的偏向。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也曾沉浸在这些世界——投资银行、国会、白宫、游说。然而,金融危机如同一场地震,给数百万人带来深切的痛苦;终于有一天,愤怒的公众开始注意到这里。现在,是华盛顿追击华尔街的时候了。
占领华尔街活动照片 图片来源Paul Stein/Flickr
❺
2010年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2009年过去,2010年到来,什么都没发生。
从那个冬天到2010年春天的几周,是康诺顿工作生涯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他在7点半抵达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回家后还在工作;他会开着笔记本电脑阅读,直到午夜。他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细读雷曼破产审查员长达两万页的报告,然后为考夫曼起草关于它的演讲。他回到了塔斯卡卢萨的起点,投身世间最高尚的使命。
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里,华盛顿已经被金钱的力量俘获。他也被俘获了;直到此刻,他才彻底理解,“影响力产业”——游说、媒体宣传、草尖和旋转门——是如何改变了华盛顿。“当你回到政府时,你会意识到,它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不对称变得多么严重。几乎没有人会走进你的办公室,试图告诉你公众的观点。”他开始把自己视为杰克·伯登,小说《国王的人马》中的叙述者,被政治玷污,对政治的幻想破灭。
人性保持不变,但当金钱水涨船高,它就会以一千种微小的方式腐化人类的行为。“华盛顿改变了我。”他说,“如果它改变了我,那么它也必然改变了其他许多人。”
康诺顿回到参议院时,曾想象拜登成为他们的关键盟友,他敦促考夫曼拿起电话,要求他的老朋友推动司法部门起诉高层,推动财政部认真对待金融改革。一如既往,考夫曼保护着拜登。华尔街不该是拜登的问题——它会占去船上一半的空间,而船上已经堆满伊拉克、经济刺激和中产阶级问题。康诺顿无法克服这种陌生感:他们的前任老板如今是这个国家的二号人物,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而他们对华尔街束手无策。共和党人原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康诺顿的不满更多是针对自己人。
康诺顿的参议院工作于2010年11月15日结束。他飞往哥斯达黎加,立即进行了一场八个小时的徒步。回到酒店房间,他打开淋浴,没有脱衣服就走了进去。他站在水流下,让它浸润身体,直到他觉得自己干净了。
本文节选自《下沉年代》,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出品。由出版方授权发布。

内容来自网友分享,若违规或者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所有跟帖: ( 主贴楼主有权删除不文明回复,拉黑不受欢迎的用户 )
进入内容页点击屏幕右上分享按钮
楼主前期社区热帖:
- 外汇储备放在哪?外汇储备有什么用? 03/29/24
- 聊聊选机 03/22/24
- 老段子新编,吹牛 03/09/24
- 【江南沙龙】趣谈英文名 03/03/24
- 趣谈英文名 03/03/24
- 闲侃吹牛 02/29/24
- 明儿还算个节日,贴两首歌吧 02/13/24
- 纠正几个ywhan“罗织”的错误 12/05/23
- “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把天体運行的规律框架搞清楚了.” 真的嘛?! 11/20/23
- the Promise Is the Promise 11/07/23
- 料、脑与货 10/19/23
- How Do You Know? 05/24/23
- Queen – Bohemian Rhapsody (Donald Trump Cover) 02/27/23
- 侃侃现在放开与继续严防 12/21/22
- 侃几句克罗地亚与摩洛哥的比赛 12/18/22
- 阿根廷vs法国历史战绩:阿根廷6胜3平3负,上届世界杯3-4法国 12/14/22
- 克罗地亚VS巴西,下半场。上半场0:0。 12/09/22
- 侃几句足球 12/04/22
- 波兰0:2阿根廷,沙特0:2墨西哥 11/30/22
- 今日两场比赛的意思不限于比赛本身 11/29/22
>>>>查看更多楼主社区动态...